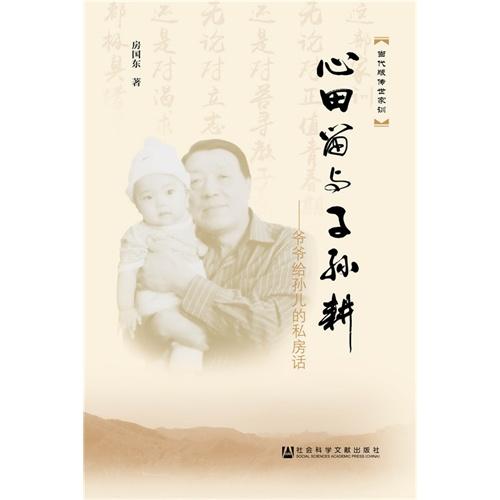在滑师的日子里
更新时间:2024-08-30 关注:581

我离开滑师已有很长很长时间,弹指一挥间,马上就快四十年了。
滑师的全称是滑县师范学校,在滑县远离县城的古镇上,当时它的四周有三面都是田野,后面有大面积的黄河遗留下来的沙丘,沙丘上长满了刺槐,蓊郁绵延,蔚然成林。一条公路从旁边通过,直通濮阳。20世纪80年代初,东濮油田刚刚兴建,路上奔驰着的多是载重的大卡车,也有拉载麦秸如山的小马车。一条淌着微水的小河在校门前蜿蜒,浅水静流,几乎听不到水流的声音,河道被水缠绕成无数的微甸,甸上满是簇拥着绿绿的青草和无数的小花,还有那飘若白云的羊、散如群星的鸟。甸与甸之间跨步可过,就像是一块块路垫,踏上去那酥酥软软的感觉,若踏云追霞般的绚丽。印象最深还是那破烂不堪的校园,到处是杂草、乱树和瓦砾,每周的劳动课,不是铲草,就是清运,但也奇怪,两年的学习时光结束时,校园里杂草仍在疯长,瓦砾遍地还是。
20世纪80年代初,那还不是太遥远的回忆。想起我的滑师生活,虽然青春灿烂,但苦寒的记忆,让我回想起来不免还有点局促,随着时光不可置疑的逝去,当年自己身上发生的肉体与渴望、生存与生活、现实与理想的冲突,时间久了,竟成为敏感的命题,总在纠缠着你的情丝,但日子常常狼狈,炫耀成功无期,每每思之,也是夜不能寐。那时候恢复高考才几年,一些新生并非直接从中学而来,而是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,所以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,最大与最小能差十多岁。忽然有了读书深造的机会,大家都很珍惜,也很欣喜。
学校的教室是两排砖混结构的老瓦房,不比我在中学时的条件好,灯管悬在空中,开门关窗凡有点风,它都会晃悠半天。还真有一次正上课呢,灯管突然掉下来,摔在地上变得粉碎,但除了引起一阵小骚乱外,所幸并未伤及到人。后来,这些灯管被几位年纪稍大的同学乘课余时间全部固定好了。我们的男生寝室是在学校操场旁新建的红砖简易平房,一间寝室挤进去20多人,分上下铺。每天晚上,在部队当过班长的雷云峰不知要吆喝上多少回大家才能静下来。睡在这样的寝室里,简直就是夏天雨后的池塘,蛙鸣十里,鼾声都能把寝室的屋顶给抬起来,但时间长了,一切都成了催眠曲。当时每间寝室学校都配了一个大塑料桶备夜用,每天的值日生负责清理与倾倒。有时,因它会产生些琐碎小事,也会在同学间产生矛盾和不愉快。那时夜静,人入睡之后,大家你来我往,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,有些人惊夜而醒多是因为撒尿声扰,脾气不好的同学会嘟囔、斥责,甚至是谩骂,由此也产生拌嘴、吵闹,甚至是打架。夏夜还好,同学多外出解手,但冬夜寒冷,尿桶满了,有的同学还照撒不管,结果搞得尿流满地,臊气盈室。值日生闹起情绪来,尿桶竟能放在寝室一天都不去动。同学们就在这满是尿臊的寝室里议论来议论去,又是立制度,又是发警告的,闹腾个不停,真像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,不仅是动口舌,还有拳脚行。
我们的学生食堂可是个大场面呢,前面有个偌大的广场。每到饭时,同学们如鱼洄流,汇集于此,排起很长很长的队,熙熙攘攘,就像个热热闹闹的农村大集。每个人买了菜买饭,买了饭买馍,馍还分着黑白,都不在同一个窗口卖,因此吃顿饭要费好多的周折才能弄齐。后来,我与三个同学组团,各拿菜票、饭票、黑白馍票,每人只用排一次队,饭菜馍四份便可全部搞定,真是节省了不少时间。再说四个人每天蹲成一圈共餐,边吃边说,边笑边乐,每顿饭都有聚餐的味道,很是温馨!也有一次,因我班一位同学买饭时受到炊事员的嘲弄,于是同学们气愤不过,群起而闹,与炊事员打了一次规模不小的群架。谁知那位炊事员竟然是老师的儿子,老师在课堂上一而再地致歉,弄得大家都十分尴尬。结果此事在全校先是当壮举传为佳话,后来又视孟浪成了笑谈。
由于学校是新建的,我们到校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,几乎没有什么古籍老版的图书,文史类的书籍都是新购的当时流行的作品,记得传阅最多的书是戴厚英的《人啊,人!》。但学校是原县委党校的底子,所以党史和马列原著多,喜欢政治的同学啃原著的不在少数。我那时也就是十七八岁,也幻想着知识可以化一切陈腐为神奇,便硬是想开辟一条路,哪怕只是到达自己的梦境边缘也罢,于是发疯、发狠地学习,总觉得自己的推理比一切概念定律都伟大,不但敢于对自己施虐,也敢于向不可能挑战。就这样蚂蚁啃骨头,硬是把《资本论》囫囵吞枣地啃完了,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些关于剩余价值方面的文章。那时,啃那样大部头的经典原著,显然是小牛拉大车,很是吃力啊!但兴趣、乐趣、情趣皆浓,所以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,还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。由于这部著作的引导,又进一步阅读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著作,这使我比较早地接触到比原著更实际、更复杂的农村改革实践。我企图以自己的行动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,似是有模有样,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,却是那样的困难,这突出反映在当时我写的一篇考察报告《不能走那条路》上。现在忆来,那是一篇用孩子的眼光和成人的语言向社会表达的一种意愿,青涩、幼稚而懵懂。那时尚未成年的自己,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涌动中,无所顾忌地过早成熟了。回想滑师两年的学习生活,那确实是一段神秘莫测的时光,那时的情感真挚而冲动,像从山崖奔泻下来的山溪,欢快而执着,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,心气很高,什么都想知道,什么都想尝试,全然不顾家庭与自身的条件限制,莽莽撞撞地把心胸彻底打开,迎接着变革时代初期的激荡与阵痛,自认为在学习和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,于是,谁先闯进心里来,就先拥抱谁,结果到后来竟然都虚无成了缥缈的云烟。好在当时教政治的刘老师,他先鼓励,后提醒,费尽心思,好不容易才把我们从好高骛远的虚幻中拉回来,但那不羁的心野,不甘现状、急于突破的心思还有,虽然没有因此成就什么,不过那份孜孜好学的因子却留了下来。
“文革”之后人才匮乏,新组建的学校,师资力量更是薄弱。我们的老师,有的是从乡下平反归来的老先生,右派帽子刚摘,教课的谨慎和小心还在,一副畏惧谨慎的形象。有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师,虽然气宇轩昂,但露怯处常有,常常把一些平时惯用的成语都读白了字。有一次,老师把姓“单”(shàn)的同学读成“dān”,那位同学当堂而起,连忙纠正。有的老师是从中学调过来的,虽然教课扎实,但脸横如板,仍像带小孩似的管教,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常常为之不屑,不服管教,不时也让他们下不了台,出现些僵持与尴尬,最后都不了了之。倒是从高校新毕业的老师,带来了一股新风,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邢老师,课堂内外与同学们交流多,身段低,相处乐,吃喝玩也常和学生在一起。有时节假日回家了,他还把自己宿舍的钥匙留下来,让一些好学的同学有个僻静的去处。师生关系相处得恰如春水。这让我想起孙犁先生在回忆他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写过的一段话:“学校的教学质量,我不好评议,只记得那些老师,却是循规蹈矩,借以糊口,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。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雷班长带人到校教导处请愿,撤换了同学们不满意的俩老师。正是这样的情况,两年的学习生活,让我记住又崇拜的老师并不多。几个调皮的同学晚自习后,在讲台上模仿一些老师上课,拖着老师特有的腔调,挥着老师招牌式的动作,惟妙惟肖地表演,常常引起同学们一片嬉笑和叫喊。当然,出老师洋相、开老师玩笑的恶作剧当场被老师逮住的也有,但训斥一番回来,脸上还是一堆坏笑,满是炫耀的神采。贾姓同学在日记上写了老师的“风流韵事”,忘记合上本,老师恰坐其位上闲看,被气得恼羞成怒,好几天都没到班上来。不管怎么样,由于“文革”荒废的时光多,总算有了以读书为荣的时代,所以同学们刻苦学习的氛围浓。当时,一个姓王的同学与贾璐同学比赛熬夜,结果终没抵过贾璐那苦学的恒心,败下阵来。那时这个小小的师范学校的班级里,做学术梦的人还不在少数呢。尽管我们当时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做专家、当学者,只是面对交织复杂的时代,在“八十年代新一辈”的激励下,深感自己的知识储备如此不足的清醒与忧患。那时候,我们有思想,但想法太多,所以杂乱如荒草;我们有奋斗,但标准太高了,所以半途而废的多;我们有追求,但目标太多又不切实际,所以纵情一歌,又常常找不准调门,觅不到韵脚。但是,“时人莫小池中水,浅处无妨有卧龙”,我们班后来还真有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和剧作家,尽管凤毛麟角,也是熠熠生辉啊!

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,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,新旧的观念此消彼长,都在慢慢地转化着,再加上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,家乡正在进行联产承包的推广工作,土地分包到户,父辈们一时从大集体的体制走不出来,他们的情绪和思想,不免会影响到学校来。当时,思想观念里阶级斗争的意识尚浓,因此根据家境、思想与爱好,同学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组、小派,还邀一些校外的人过来谈诗、谈政治 、谈表演和戏剧……思想异常活跃,清谈气氛浓厚,行为也多有点率直,又喜欢雅集,常喝酒纵歌,喝得你不是你、我不是我的。那微醺小醉的样儿,现在想来还是那样的美妙,确有陶潜“我醉欲眠,卿可去”的洒脱。下苦功夫的同学悄悄创作作品的也有,那时年轻气盛,扬帆风满,心比天高,竟瞄准经典著作挑刺或颠覆。贾璐同学两年内自学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,尤其对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汉语》下功夫最大。在读《晋灵公不君》时,对王力先生解释的“置诸畚”有疑,便去长信给王力先生,提出自己的见解。王力先生很快回信,给予他热情洋溢的鼓励,并介绍《春秋公羊传》给他看,这在全班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受此影响,读原著的同学也有不少对正在阅读的经典提出自己的疑问来。那时,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不时会给某位同学发来信函,大大长长的信封,格外地显眼,但内容大都是信已收到、表示感谢之类的话,所提建议被采纳和肯定的未再有例,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影响同学们求知求学过问政治的热情,于是心思更大的同学竟然写起了体量更大的论文。我们班这一有点悬空的情况,引起了校党委的高度重视,班主任也苦口婆心地讲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知识、打基础,不要脱离实际。校方还适时在校广播站开设诸如《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》之类的专栏予以播放,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。同学们利用这些阵地,还有黑板报,也争论一些问题,有时竟敏感得令人不安。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建立又不断毁灭的过程,人物也好,事件也好,不断地去接受,又不断地在颠覆,心里始终没有一个长久的、稳定的东西作支撑,所以内心的矛盾总是将该要显示的方面都给抵消殆尽。那时把追求反思与探索为旗帜的朦胧诗派当作崇拜的偶像,几个同学成天价日地把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挂在嘴上,好像不来点忧郁就不算成熟一样,倾情自己,忧虑未来。当时,同学们开始对课本里主张的思想怀疑起来,常常出现“原则性的分歧”,什么理论呀,观点呀,在争论时,大都是自命高深,像占领高地一样,冲劲十足,互不让人,个个金刚怒目,叱咤凌厉。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凭借阅历深邃,似有洞彻之见,语言犀利,常常唬得我们不敢开口接话,对于人物的评价都溢出了当时的语境和口径,一些同学因此争得面红耳赤,气愤难平,甚至积怨致恼,一言不合便会拔剑而起,所以也因争论发生过小斗小殴,但也没有产生出领袖群伦的人物。还有一次,因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,大家兴奋难耐,热情难以遏止,便组织了一次游行,喊着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,向着街上走去。大门夜锁不开,便翻门而出,在夜色阑珊、行人稀少的古镇老街上转悠了半夜,才兴高采烈地回来。所有这些都让校教导处的老师摇头称苦,说这班文科生就是不安分啊!当然,由于不堪承受之重,那时候同学留下创伤的也不少,不仅有政治方面的,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有,什么流产的纪念会、生煤火事件、臭豆腐风波等,以至于30多年后谈起那些往事,很多同学还是感慨万分。其实,那些微伤的记忆,都是因为当时那个来历不明、虚无缥缈的梦啊!
当时学校的文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。学校定期举行文艺演出,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参与的积极性很高,有写剧本的,有练歌舞的,有排小戏的,走幽默一线的还演练着哑剧和相声。大同学郭睿的小提琴,时常撂在床铺上,一有空闲就拉上几曲,婉转悠扬,时而清脆如群鸟齐鸣,时而倾泻若泉水叮咚,不徐不疾,得之于手而应于心,口虽不能言,而乐尽解人意,功非一日,艺已成塔,水平已是相当高了。因此,我们班在校文艺演出中屡屡获奖,出够了风头。近40年了,同学们见面还称呼着他们在舞台上角色的名字呢!当时,每逢周六的晚上,在校大门外的土路上就会放一场电影。同学们与周围的村民聚集在一处观看,夏天天气炎热,人头和蚊虫攒动是影,人有动作,或是风儿掠过,都会飞扬起一片尘土,没风的夜晚,还会热得一身透汗。那些好表现的同学,放映前在镜头里剪裁几个夸张的动作,映在银幕上。寒冷的季节,很少放映电影,露天太冷,观众边看边跺脚,比电影里的声音还要大。放映员穿着厚厚的军大衣,也是抵顶不住,所以草草收场的多。看电影时,夏天的夜虫纷飞与冬季的雪花曼舞,都成为我们天赐的浪漫记忆。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小同学,与幼师班的女同学已开始在一起学跳交际舞了。夜已很深了,满寝室的老大哥们都睡不着觉,专等着那位韩姓的小同学回来绘声绘色地叙说学舞的趣事,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夜都深了,兴奋的劲儿还下不来。老班长一反常态,没有批评和制止,而是一声不吭地倚着床头闭目养神呢!
那时,班里学习气氛浓还体现在刊物的征订上。班里50多人,订阅的各类刊物超过了80份。一位姓刘的同学订了3本诗歌刊物。刚入校时,他写了一首爱情诗给我看。诗分为三节,以两年学习时光为背景,层层递进,向渴望的爱倾吐心声,最后一句我依稀记得:“把情致凝到枝头,只待春风。”很显然是写他中学时代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,只是不知道他凝在枝头的那番情致,这么多年春风是否吹拂呢?在滑师期间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,就是身上带有浓郁诗人气质的巩姓同学,把他写的一首诗邀我去看。我的天呀!政治抒情长诗,厚厚的一大本,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略带飞草的字迹和长短不一的诗行,带着他的理想、才情和辛劳,竟然布满那个笔记本的每页纸上,初初捧读,便觉分量是沉甸甸。那些日子,他有点忧郁,常常在夜色里、月光下,独自在槐林里漫步。我与他也去找过教写作的老师,渴望指点,寻求发表。老师肯定那首诗见解独特,发人未发之见,抒人未抒之情,只是内容上有点偏激和敏感,但叮嘱他多投投稿吧,或许会涌入哪位编辑的法眼呢!从师范毕业后,虽然也见过他两三面,但光顾同学间的攀谈与热闹,未及问他那首长诗后来是否发表,现在还在写诗吗?
我那时虽也喜爱文学,但专心的却是中共党史。前些日子翻起一大堆笔记,全是我当年关于党史方面的摘录。我当时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,也是因为说好了能在党校谋一差事才去的,谁知经过两年的折腾,却调到县委宣传部搞起了新闻,因为工作需要接触起文学。同学中也有持之以恒、不改初心取得正果的。贾姓同学在学校时就写剧本,后来参加工作也搞戏剧创作与研究,且成果丰硕,几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华奖,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,佳作纷繁如云,荣誉灿若夏花,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剧作家之一。业界笑谈他到哪里,舞台竟然会无灯自亮,可见人家的辉煌是自带流量的。我的诗集《月舟集》便是请他作的序。现在,他盛名戏剧界,所以也因名而累,成年天南海北地跑。去年,他新创作的两部戏剧好评如潮,惊爆了全国的戏剧舞台。这是我们这些浮漂之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是难于做到的。他过去也常来我处闲谈,话题很广,谈得很深。我常常把思想、生活、工作的苦恼给他诉,他听得很投入,劝得也很耐心。我虽愚钝,但他的兄长风范、谆谆之教,我是不敢稍忘的。只是这两年各自在工作和事业上忙碌奔波,相见多是在微信里。
年轻人在一起,最有趣的要数谈恋爱了。进入二年级,男女同学接触一多,再加上与纯女生的幼师班联谊活动的频繁,便传出不少的恋爱趣事。有奔放热烈的,如班长与幼师班长“老夭”的恋爱,竟然成了两个班友好的纽带。特别是“老夭”,满口外交辞令,还应邀到我们班讲过话,而且很大方地邀请更多的男同学到她们班里去联欢。也有缠绵悱恻的,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单相思,一方痴痴冥想,苦苦单恋,一方竟然大大咧咧,全然不知,愁得那老兄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,苦无办法。有的厚着脸皮去求爱,当面被冷拒之后,呼天抢地哭个不停,悲痛欲绝的样子令人心碎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也有,如趁女同学不注意偷偷塞个小字条什么的,结果被顽皮的同学捡起来,在教室里当众宣读,惹得满身是骚……那一段时间,同学间一会儿谈奇闻,一会儿谈趣事,花边新闻很多,绯闻接连不断,故事的主人公像唱戏似的换来换去,以至于毕业多年,班主任做了我的上级领导,在一次闲谈中,他向我求证了当年关于这方面的很多事。啊,原来他也了解这么多呀!其实,那个热热闹闹的恋爱季过后,真正成为伴侣走到一起的,反倒是当时默默无声的刘保仁和王文华同学,其他叽叽喳喳满天乱叫的人,基本上都是恋爱彩排。年龄大、城府深的郭睿同学,虽然常常笑而不语,成天把小提琴拉得回肠九转,惹得大家情感萦绕而解脱不得,谁知道他那时已是做了父亲的人,心事比我们更纷繁、更具体、更焦灼、更深沉。许多年过后,那时的恋爱趣事,皆已成了笑谈,也只有影子记得,故事留下,但人物都已模糊了。是啊,没有憧憬和期待,谁还会再去品味那些尴尬呢?
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活,细细想来,引发我许多念旧的沧桑和感伤。史侃《江州笔谈》卷上云:“学生二十岁不狂,没出息;三十岁犹狂,没出息。”狂与不狂,不是人生的状态,也不是年轻的标签。它不光与年岁有关,更与未经琢磨过的心野相连。心间空空,多以狂补。摄取的知识多了,阅历广博了,心反倒能够静谧如月。当时面对的现实,往往超出了我们能够衡量的尺度,宛如老虎吃天,真是无从下口。因此,失意时,锥心裂肺地痛苦;得意时,也兴高采烈地喜悦;但感到彷徨的是苦苦找不到人生的支点,撬不动自己想要撬动的一切,当理想魔力日损于平淡无奈的日常时,才知过去的一切拼搏都显得苍白无力,而且闪现每一个念头,都有可能把过去完整的画面撞得粉碎。唉,不提它了。现在,有的同学已经去世多年,有的已经渐入老境,有的还在奔波打拼,有的已经声名日隆,但大部分人还是默默无闻,人生的一切都没有按照在校时想象的路径走。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奋发,甚至挥斥方遒的轻狂,俱往矣,好像都在梦幻里。也许我还要写下去,除了写点小东西,我还能干点什么呢?人生得失,事业成败,未及思量,恍惚之间,一生一世就要这样耗完。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。当时,一方面不甘平庸,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时代的开端,心存向往,处处勃发着生机;另一方面又感到困惑的东西不少,有劲儿无处使,所以,只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溜达溜达,倾听一种可以自我安慰的心跳。然而,出生决定未来,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,一出生,一切就已前定了,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,长在“文革”动乱岁月,长大又进入改革年代,一切机遇和可能,像初春的山坡,到处是绿草和花朵。然而,根据我的秉性,不会竭力去嘶喊:“请滚开,让我歌唱80年代!”
在全国大中专院校纷纷升格之时,我的滑师却变成了一所中学。前些日子,组织上要求对文凭进行重新认证,我找到学校时,过去的旧迹百寻不见,就连原来学校象征的公章都没有了。物非人亦非,名实皆亡,一切已然苍茫。离学校不远处,原来那片低洼的土地,现在粼粼而成浩瀚的水面,水光潋滟,画桥烟柳,亦称是西湖。那段当时还在漕运着的大运河,不见了帆影桨声,却成就了一处名胜。还有周日闲逛过的旧街老店,现在开发成了著名景点。离开学校近40年,时常想起那些飘忽着的旧景和形象斑驳的师友,这一切虽像新台旧戏般的消散,但毕竟还有依稀的记忆在,不过也是大者不知,小者不详,只是一些片断了。可惜,关于滑师、关于滑师的学习生活,直到它消逝多年之后,我亦日衰渐老之时,才想起它……
(本版图片提供:齐丁友)
作者简介:王兴舟,笔名东坡石,诗人、作家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,多家报刊专栏作家等。连续三年荣获河南省报副刊一等奖;先后荣获蒲松龄文学奖散文集一等奖、蔡文姬文学奖散文一等奖、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文地理散文大赛一等奖、首届李清照文学奖一等奖等。文学创作成绩喜人,已出版有诗集《月舟集》,散文集《贮云集》《那时花开》《太行风土小记》等专著。作词了歌曲《太行·朝阳》《那里是哪里》。三十年来坚持文学创作,作品曾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求是》《半月谈》《散文杂志》《作家报》《统一战线》《中国现代文化报》《莽原》《科技信息报》《杂文月刊》《河南日报》《安阳日报》等国家、省、市媒体多次刊登。
-
下一篇:【王雷生】仰望
-
·陈才生 | “老树新花,故纸新画”——谈王兴舟的读书观2024-08-27
-
·诗意人生的感悟与吟唱2024-08-30
-
·【视界晨报】“寻福记”名家漂漆书法与植物画非遗作品展在福州成功举办2024-08-25
-
·陈宝璐|于最美的秋天里,收获岁月的深情(美文)2024-08-25
-
·瘦石先生词十首2024-08-22
-
·【实力派作家】屈光道|谷雨云诗六首2024-08-22
-
·河南安阳:殷都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开展“中医科普大讲堂”活动2024-08-21
-
·【视界晨报】热烈祝贺孙喜民被山东省散文学会吸收为会员2024-08-20
-
·【视界晨报】李士文|诗词三首2024-08-20
-
·【视界晨报】安阳仁康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庆祝第七个中国医师节活动2024-08-19